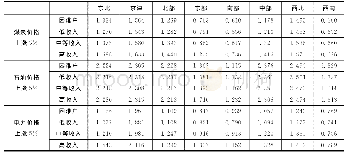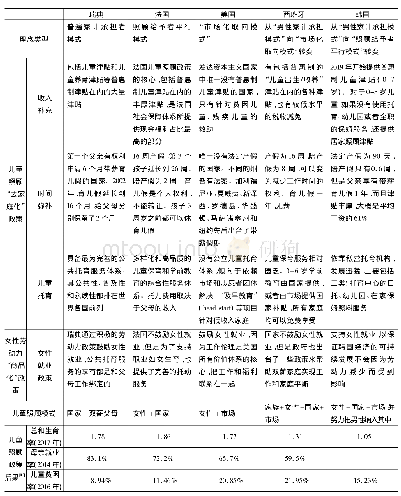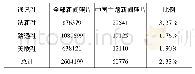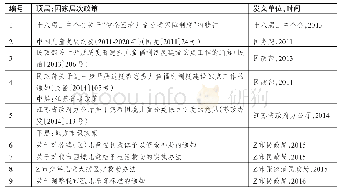《表1 西方三大福利体制的儿童照顾政策》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本系列图表出处文件名:随高清版一同展现
《育儿责任、性别角色与福利提供: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展望》
福利国家育儿责任的制度安排囿生于公民共识的达成。[11]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将家庭视为儿童照顾的唯一主体,对于家庭育儿边界的任何侵犯都被理解为扩大国家权力的手段。后来,家庭通过市场的自由购买来实现儿童责任的少量外化。但随着“避难者之家”(House of Refuge)、“玛丽·艾伦”(Marry Ellen)及“少年法庭”(The Juvenile Court)等三大儿童保护运动的兴起。[12]人们囿于对儿童虐待等成人恶习的厌恶而逐步放松了育儿的家庭界限,使得国家参与儿童照顾开始得到民众理解。自20世纪下半叶起,基于人类需要和政治斗争而形成的公民资格观进一步促使现代福利国家更加珍视公民价值,社会权在领域上的逐步拓宽深化了各国的“去商品化”程度。以新西兰《儿童与青少年法》(1974)、澳大利亚《家庭法》(1975)、美国《儿童虐待防治与疗救法》(1974)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都加大了儿童照顾的国家介入能力。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女性就业率的增加及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性别平等视角下的女性主义思潮对于公民的福利共识带来了新的冲击,福利国家的儿童照顾政策再次经历了重大的转型。英国《儿童法》(1989)、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89)、德国《儿童与青少年福利法》(1990)、韩国《儿童福利法》(2000)等一系列政策都在托育服务、财政津贴、税收减免及育儿假期等方面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当然,由于对于公民社会权的范畴和规模仍然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福利国家的各种变型并不没有呈现出直线型分布特征,而是依循体制形态不同的类属而存在”[13]。因而,三种福利类属下的儿童照顾政策仍和而不同(见表1)。
| 图表编号 | XD0064149300 严禁用于非法目的 |
|---|---|
| 绘制时间 | 2019.04.01 |
| 作者 | 李向梅、万国威 |
| 绘制单位 |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
| 更多格式 | 高清、无水印(增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