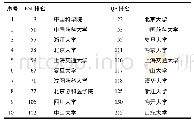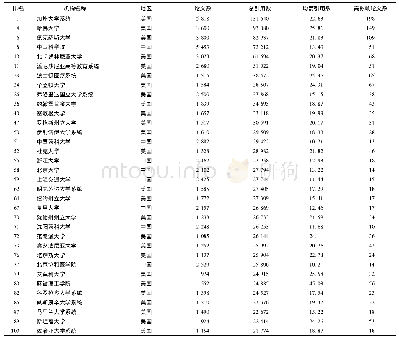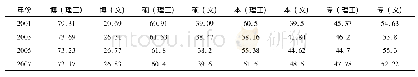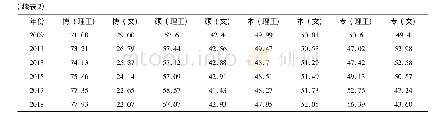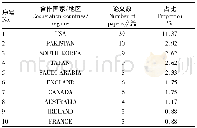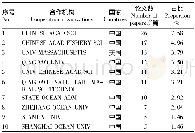《表3:燕京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滥觞》
说明:本表由作者提取《燕京大学课程一览(1928—1929)》30中的相关信息绘制而成。
其三,重视写作课,注重新文学的“创造”。1931年12月3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演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时曾经指出:“近四十年来,在事实上,中国的文学,多半偏于考据,对于新文学殊少研究……文学有三方面:一是历史的,二是创造的,三是鉴赏的。历史的研究固甚重要,但创造方面更其要紧,而鉴赏与批评也是不可偏废的”34,这是作为新文学倡导者的胡适对于文学状况的基本认识,同时也对当时大学重视考据和历史研究而忽视新文学创造的倾向提出了含蓄的批评。在这样的语境中,燕京大学正好提供了另一向度的尝试。早在1922年,燕大校方即在写给管理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将“新文学部”目标概括为“培养受过训练的作家”(with the object of producing trained writers)35,虽然后来“新文学部”的学科建制被取消,但其宗旨和课程依旧被保留在了燕京大学后来的课程计划中。无论是“每两星期作文一次”的“名著选读”、“以白话文为限”的“习作”以及“注重练习以求实用”的“修辞学与作文”,还是“近代文学”“新文学之背景”“近代文学之比较研究”等课程中渗透的对新文学写作经验的总结,都无不贯穿着对“新文学创造”的注重。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抱整理国故之志愿,而益有创作才能”36亦成为许多燕大学子的学业追求。
| 图表编号 | XD00112958500 严禁用于非法目的 |
|---|---|
| 绘制时间 | 2019.10.15 |
| 作者 | 王翠艳 |
| 绘制单位 |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
| 更多格式 | 高清、无水印(增值服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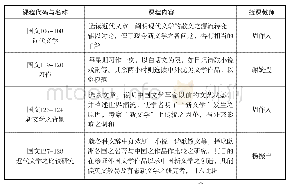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